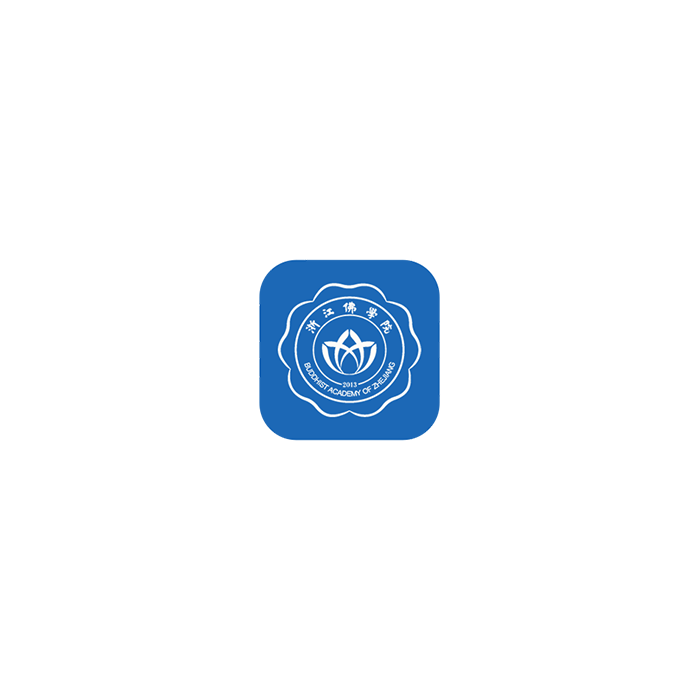丝路沿线文化交流中的弥勒信仰

来源:雪窦山

时间:2022.02.22
文丨吴小丽
摘录自《法音》2021年12月刊
丝路沿线不同地域的文化,对弥勒信仰的形成、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丝绸之路上,以敦煌为中心向四的波斯等国家的文化中,亦可以看到弥勒文化信仰的痕迹。季羡林先生认为,弥勒“在印度、中亚与中国等地的佛教神坛上占有突出的地位”【1】。“信仰是人类精神的核心行为。这种意义上的信仰,并不是指人类精神的一种特殊行为,也不是诸多因素及其功能的总和,而是超越于各种特殊的因素、功能及其总和的,可它本身又对人类精神的各个部分有决定性的影响。”【2】从弥勒信仰传入中国的进程之中,可以看到它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僧团本身及社会等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丝路沿线西行与弥勒信仰
(一)古印度弥勒信仰与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涉
关于古代印度弥勒信仰产生的时间和地点,学界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但学界普遍认为,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及考古成果来看,弥勒信仰曾在古印度西北地区尤为兴盛,西北古印度在弥勒信仰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孔兹(Conze )就提出西北古印度犍陀罗地区是弥勒信仰的中心;季羡林先生认为,弥勒的形象形成于古印度西北部,并指出从词源来看,弥勒(Maitreya )与伊朗密特拉神祇(Mithra )是同源的,弥勒信仰从早期重点强调“授记”成佛,发展到后来特别突显其“未来佛”的身份特质,可能受到当时传入西北印度的西方“救世”思想(messia)的影响,即与弥勒未来佛融合在一起,并推动了后者的发展。
不过,李玉珉等学者也指出,弥勒(Maitreya )与伊朗密特拉(Mithra )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名称的,仅仅是语音上的相似,弥勒未来佛是基于大乘自性平等、无我利他慈悲观基础上的以“法”救度众生的“救世观”,而与西方基督教、拜火教“终末论”上的“救世主”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所以二者在基本教理、宗教功能及图像等方面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上,西北印度作为东西方文化深度交汇融合的地区,古代弥勒信仰在此与其他西方宗教文化彼此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如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大成佛经》中有“梵天持天香油灌摩诃迦叶顶”的文字,而印度文化传统中一般是用水而不是香油灌顶。上元和认为,这种用香油进行圣别(灌顶),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影响。此外,弥勒早期的交脚菩萨形象,与波斯的国王、神衹形象的坐姿也类似。尽管如此,这种影响更多的是表象层面上的,而在信仰内核上,弥勒信仰与西方宗教的救世思想传统存在根本上的不同。
(二)弥勒信仰与南传佛教
佛教诸多典籍中,涉及到弥勒的经典有37部。在最原始的佛教文献中,弥勒是佛的弟子,还不是菩萨和未来佛的形象。
早期小乘佛教中并没有菩萨崇拜,只是把菩萨果位看作是佛陀觉悟之前的一个修行阶段。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若礼菩萨读大乘经,名之为大,不行斯事,号之为小。”【3】可见,小乘佛教没有主张必须礼敬菩萨,也就不可能有崇拜弥勒菩萨的现象出现。
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和阿含部经典,如《佛本行集经》等,这些经典中多用:慈氏、梅怛俪药、梅呾利耶等称谓指代弥勒。用弥勒来与释迦牟尼作主次对比,起到突出释迦牟尼是主尊的作用。即使在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涉及到弥勒部分,依然主要是以释迦牟尼与阿难、弥勒等弟子之间的对话问答展开,弥勒身份也还是释迦摩尼的弟子,这些小乘有部等经典中显示了弥勒和佛之间的地位差距。
(三)弥勒信仰与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中提出的修行实践道路主要是:罗汉一菩萨一佛陀,这样就有了菩萨崇拜出现。因为弥勒身份特殊,其信仰相比其他菩萨的信仰要早。记载弥勒的佛教典籍一方面是从原始佛教传来,另一方面大乘佛教继承前者之后又有发展,并反过来影响到小乘的阿含和有部等经典。
对弥勒信仰的具体理解,大乘佛教和小乘有部之间存在分歧。例如:玄奘西行求法时,龟兹教派的高僧木叉毱推崇《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玄奘西行求法时索求弥勒《瑜伽师地论》,木叉毱对弥勒及其经典表示不认可,两者之间引发辩论,但最后玄奘辩论胜利,并令木叉毱信服。
大乘佛教发展的后期,又出现了弥勒净土和兜率天,千亿年后弥勒下生娑婆世界,将在龙华三会中度化众生,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前壁中,就绘有弥勒说法图。这样弥勒信仰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在鸠摩罗什翻译的《弥勒大成经》与竺法护翻译的《佛说弥勒下生经》等中都有体现。
可以看到,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加上佛教思想体系中的大乘、小乘思想,至此,弥勒完全具备了三重身份,即佛弟子、八大菩萨之一和未来佛,后者是释迦牟尼亲自授记和预言:弥勒将会成为未来佛并在人间建立净土世界,这些内容在高昌回鹘时期的石窟图像等资料中都有体现。
蒂利希在讲述有关宗教信仰时,提出终极关切和终极关怀之说,他认为:“所谓的信仰,就是指某种终极关切的状态。”【4】弥勒信仰多重身份的出现,也是不同层次的信仰者对终极关怀的一种强烈渴望和期盼。
二、丝路沿线向东与弥勒信仰
“在佛教东传过程中,弥勒信仰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5】汉传佛教,对弥勒上生、弥勒下生都有所接纳并产生信仰;加上在民族与民俗化的信仰中,以五代僧人契此为原型的大肚弥勒的出现,展现出弥勒信仰在不断发展中产生了不同向度的具体形态。
( 一)道安的弥勒上生信仰与法显的弥勒下生信仰
汉地弥勒信仰,始于四世纪道安。道安的弥勒上生信仰与他对般若、禅法等思想的融合和会通分不开,道安主要弘法历程与弥勒思想也密不可分。在中国的佛教史上,东晋时期的释道安是一位领袖式的高僧,他一生致力于般若学说,同时又兼顾小乘禅数之学,他最终立誓并发愿往生到兜率净土。
道安的弟子众多,方立天所著的《魏晋南北朝佛教》中认为:“长江流域都遍布了道安的弟子 。”【6】道安的弥勒信仰,与他所肩负的使命有关 ,他希望为僧团的发展提供可以依赖的经典依据 ,同时也与他所兼备大乘佛教的积极入世精神有关,希望往生到兜率内院,等到弥勒再次入世成佛并教化众生时,可以选择追随和共同教化。道安的弥勒信仰在《高僧传·道安传》中有记载,文曰:“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 ,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7】同书的《高僧传 ·昙戒传》中,也讲到道安的弟子:释昙戒,“后笃疾常诵弥勒佛名不辍口。弟子智生侍疾,问何不愿生安养,诫曰:'吾与和尚等八人同愿生兜率,和尚及道愿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愿耳。'言毕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悦。遂奄尔迁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8】
其中的“安养”,是指阿弥陀佛的西方世界。因为,他与道安等人之前已经有约定了,所以昙戒不愿往生到弥陀净土,而是要共同往生到弥勒的兜率净土。因此,弥勒净土信仰的雏形,在道安那里就已经出现了。也可以说,慧远的西方弥陀净土信仰,是其老师道安的弥勒净土信仰的一种再次延续。如果说“文化把许多个人转变为有组织的团体,而使之无止境的继续存在”【9】,宗教中的信仰文化也是如此。
法显西行求法归来后,所撰写的《佛国记》中记载,他是想把有关弥勒下生信仰的经典带回来,只是没有写本。法显对弥勒下生的信仰也由此确立。从晋末宋初开始,西行求法的运动开始被僧团们热衷,求法的也多是佛学素养深厚的僧人。他们把最初的弥勒信仰,沿着丝绸之路的南道和中道,东传至新疆于阗、粟特、回鹘、龟兹、焉耆等地,从这些地方考古挖掘时,所发现的与弥勒相关残卷中,可以看到其影响。
法显归国后就在彭城建立了龙华寺。龙华寺,自东汉以来,楚王刘英在统治彭城时,就非常崇尚佛教与黄老之学。东汉末年,笮融又在此大规模建造佛寺,有三千人共诵佛经的宏大场面。法显西域求法回国后,又再次于此处建立与弥勒信仰有关的龙华寺,大力弘扬弥勒下生信仰。
法显,还把此次西域之行艰险的经历与各种各样的见闻,写成了《法显传》(别名《佛国记 》)。据此传记所记载的法显西行中主要活动有:法显礼拜与弥勒信仰有关的圣像、圣迹等;听到有关弥勒成道时“佛钵四分”的经典;礼拜释迦牟尼佛的成道、传法的种种圣迹;礼拜大迦叶尊者(迦叶尊者是等到弥勒下生成佛之时传衣钵与他 );以及在瞻波国聆听天竺道人口诵有关弥勒的经典;并从狮子国带回当时汉地还没有的《杂阿含经》《长阿含经》《杂藏》等梵本经典。
(二)玄奘的弥勒上生信仰与民间弥勒下生信仰
玄奘,一生皈依弥勒净土,也是法相唯识宗的创立者。西行印度时,他“会通佛教大乘空、有两宗的歧义”,尊奉、学习《解深密经》等经典。他最为世人称颂的是:不仅创立唯识宗;又是学贯中原南北、大小乘学说的佛教思想家;西行求法中,调和印度大乘空、有两派,力破各种论敌,享誉西域。印度佛教沿着丝绸之路的东传,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一次规模恢宏的文化输入历程;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之后的一种文化再造运动。《法苑珠林》第十六卷和《诸经要集》第一卷都讲到,玄奘是积极倡导弥勒净土信仰,即在家俗众、出家的僧众都可以修持“弥勒业”。因为弥勒净土“其行易成”,因此“大小乘师”都可以奉持。即:“玄奘法师云:'西方道俗并作弥勒业,为同欲界其行易成,大小乘师皆许此法……故法师一生已来常作弥勒业,临命终时发愿上生见弥勒佛……所居内众,愿舍命已,必生其中。'”【10】玄奘自知“死期已至”,圆寂前发愿往生到弥勒净土。
窥基的弥勒净土信仰,继承了玄奘的唯识学的理论基础,并结合自己的实践做了一些新的发展。自魏晋时期以道安为代表的弥勒净土上生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初次繁荣之后,以唐代玄奘、窥基等为代表再次复兴。
以法显为代表的弥勒下生信仰,因为很容易被古代下层民众作为起义借口所利用,所以被统治阶层所提防或抑制,这些都导致弥勒下生信仰难以持续。
上述几位具有深厚学养的僧人,祈求往生弥勒净土的类型主要有三种:其一,上生兜率天,祈求解决疑难问题,或是判定是否得戒,而发愿往生到弥勒内院;其二,由于一些僧人神奇的渲染、讲述梦中见到弥勒并感应到不可思议的景象,受到启发触动而生起弥勒的信仰;其三,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布施、启请、供养等行为,不但可以上生到兜率净土,还可以像弥勒菩萨一样被佛授记,在未来某个时期能得到不可退转的佛果。
(三)儒释道、禅净合流与弥勒信仰
弥勒信仰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没有消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它不但解决了“死”的问题(命终后可到达弥勒兜率天),还解决了“生”的问题(弥勒成佛后的人间净土),因为其落脚点是在人间,是以建设人间理想王国为最终目的。弥勒佛出世时的人间净土与兜率净土的不同之处在于:“同样是死后往生净土,实际上却并不一样:一个是生于现世的净土,另一个是生于天上的净土。”【11】弥勒信仰也在不断与汉文化碰撞、交涉、融合之中,逐渐呈现出中国化、民族化特征。
梁代傅大士,被看作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弥勒化身。他的典型形象“道冠儒履释袈裟”,被大众认为,这是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本土的一种融合和显现。傅大士的形象之中,也就代表着儒释道的文化。
五代时期,出现了大肚弥勒佛的化身,即契此和尚,他的传法行迹,传达出当时禅宗与净土思想合流的趋势。弥勒信仰在中国化的进程中,首先是形象的演变,从最初北魏时期菩萨装束的交脚菩萨造像,到倚坐佛装的古佛形象,再到完全定格于中国本土化、民族化的,以契此布袋和尚为原型的大肚笑弥勒,被上层统治阶层和下层广大民众普遍接受和尊崇。
三、社会价值和当代意义
弥勒信仰,在东西文化交融之下展现出来的多元化的形式,对此进行探索,可以为更好地服务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并架起服务于丝路文化发展与加深各国友谊的桥梁。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地域中,有关弥勒图像主要分布在:敦煌石窟绘塑、敦煌遗书、北凉石塔等。其中弥勒经变更是跨越隋代、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等,较为充分展示了弥勒信仰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下,沿着丝路传播进程之中,对文化的双向交流互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各种宗教行为,不论制度化的宗教还是心灵里的活动,都是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12】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也以不同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
弥勒菩萨是以“大慈弥勒菩萨”为社会形象的,也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形象大使之一,其塑像普遍供奉在汉传寺院的天王殿中。挖掘弥勒信仰的社会价值和当代意义,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精神和文化。马林诺夫斯基讲到:“宗教信仰可以使个人摆脱其精神上的冲突,而使社会避免瓦解的状态。”【13】这也可以看作是宗教信仰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之一。
大肚弥勒信仰的形成,体现了汉民族自古以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他的宽容大度、积极乐观的精神旨趣,是被大众广泛喜爱、崇拜的原因;人们也不再局限于一味地向往他方彼岸的净土世界作为人生的归处,而是期待能够在人间建设庄严世界的美好愿望,体现出了宗教的人文关怀和积极入世的普世情怀。在这些专属中国佛教的本土化、民族化弥勒信仰中的积极因素,与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相吻合的,同时又在调节社会矛盾、缓解人们精神问题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大肚弥勒更是显现出众生本真自性的一种智慧,显示出了一种包容自信、超越自在、从容潇洒的生命态度与情怀。这些积极因素,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一定能够提供文化与精神上的支撑。这些文化财富,在提升社会道德伦理、人们的精神境界、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都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原有的思想相接触,不断变化、不断发展,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新学说。”【14】弥勒信仰内涵的不断演变,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目前在汉传佛教地域,弥勒信仰以中国化和民族化的大肚弥勒形象和信仰形式广为流传下来,不同于蒙藏等地区多见的天冠弥勒,这既有民族特色,展示出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也展示出各具特色的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更充分体现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国文化特色。
(作者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研究员、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本文系贵阳市科技局贵阳学院专项资金资助;2021-2022北京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YU-KY-〔2021〕)
注释:
[1]季羡林:《梅呾利耶与弥勒》,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125页。
[2]张志刚著:《宗教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3]《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大正藏》,第54册,第205页。
[4]张志刚著:《宗教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09页。
[5]季羡林:《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载《文史哲》,2001年第1期(总第262期),第6页。
[6]方立天著:《魏晋南北朝佛教》,载《方立天文集》卷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7][8]《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35册,第353页,第356页。
[9][13]〔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第76-77页。
[10]《法苑珠林》卷十六,《大正藏》,第53册,第406页。
[11]〔日〕松本文三郎著,张元林译:《弥勒净土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2]张志刚著:《理性的彷徨》,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
[14]吕澂著:《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